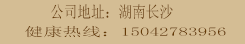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后遗症 > 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后遗症 > 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

![]()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后遗症 > 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后遗症 > 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
大便难是解大便困难,艰涩、粘滞难出,包括了大便干燥之便秘,也包括了大便不干,或稀、或软之排便困难和排便不畅、不尽。秘者,藏之于内而不出之谓也,顾名思义,故凡是大便困难的临床症状,都可以称之为便秘,但因病人习惯认为大便干燥是便秘,故本节不用便秘而用大便难,来概括具有大便困难的临床症状。近二十年来,人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便难在门诊成上升趋势,小儿更为常见。
“肠澼”、“滞下”具有大便困难的基本特征,是中医古代的疾病名,后又称之为“痢疾”。《温热赘言》:“古之所谓滞下,即今之所云痢疾也。”痢疾和肠澼、滞下有所区别,肠澼、滞下可以因为痢疾失治,或治疗不当、留邪于肠而成,也可不因痢疾而自行发生,三者有相通之处,但病势不同,病性有差异,病位有区别,应该将它们区分开来。
1.1.1临床症状确认大便难的基本特征是解大便困难,努挣难出,解便时间很长,便后多小腹不舒,有不尽感。肠澼、滞下和泄泻都有大便次数增多,但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泄泻大便泻下易出,肠澼、滞下则排泄困难、大便不尽、便后不舒。
大便性状是多样的,有的干结如珠,有的干硬而粗,有的软而不下,有的稀而沾滞,有的夹有粘液脓血。解便时间也有不同,有的每天都有便意,可以天天解便,或一日数次,有的数天才有便意,甚至根本没有便意,完全依赖泻药,吃泻药才能解便,到后来就是吃了泻药也没有便意了。若丝毫便意都没有,治疗就极其困难了,缺乏滴水穿石的韧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朝秦暮楚,都很难收全功。
痢疾、肠癖、滞下的临床症状大多相似,中医文献多合并讨论。《类经》:“肠澼一证,即今之所谓痢疾也,自仲景而后,又谓之滞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脓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里急后重者,有呕恶胀满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热往来者。”根据近代认识,痢疾为新病,发病急,病程短,是外感湿热、疫毒之气从口而入谷道,伤及大肠所致,发病多急,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多伴有恶寒发热等症,除了疫毒所致者,一般比较容易治疗;肠癖、滞下为久病,起病慢,病程长,并非外感时邪所致,没有明显的季节规律,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和痢疾虽然同为湿热所伤,但肠癖、滞下先有大肠传导通下的因应调节失常,后有湿热内生,其湿热伏于大肠血分,阻碍气血流畅,阻滞气机,治疗比痢疾困难。
痢疾有休息痢、有时疫痢、噤口痢、热痢、寒痢等等的不同,肠癖、滞下的病机变化较小,证候病机相对稳定。中医文献中的休息痢,也反复缠绵,但一般是由急性发作,治疗不当,湿热留伏肠间所致,病机和肠癖、滞下相似。
如今痢疾较为少见,但肠癖、滞下不少,若经结肠镜检查,大多有溃疡性结肠炎,或者结肠息肉等。溃疡性结肠炎发病以欧美为多,结肠息肉以前也很少见,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门诊肠癖、滞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1.1.2临床病机求证大便反应谷道升降出入之“出”的生命状况,影响“降”的气机,是体内糟粕、毒素外出的重要通道,关系后天之本的气化活动。不能出则不能入,日久气血津液没有充养之源,成虚实夹杂之证。大便难一要早治,二要坚持,治本为上,促使阳明大肠传导因应调节机制的康复,使当出者顺利外出,谷道的升降出入才无碍滞。
大便难日久不治,会壅塞中焦,危害肝之疏泄,反过来,脾胃升降和肝之疏泄也影响大便排泄。大便难是“六腑以通为用”失常的反应之一,体现了五藏“神机”协调性在“出”这一方面的异常,中老年人,可能是阳明脉衰,大肠气化活动减退的反应。明·孙文胤《丹台玉案》:“少壮之人多患秘,以其气有余而不及运转也;衰老之人多患结,以其血不足而大肠干燥也。”“大法秘者调其气,结者润其血,而秘之得于风者,即于调气润血药中,加祛风之剂则得之矣。”
从多维联系的整体观来看,大便难的病机是多样的。病位,与肝之疏泄、肾之藏精、心之血脉、肺之肃降等相关;病邪,与湿热、痰瘀、郁气、风等相关;病性,有精血之虚,有阴液之耗,有湿热之阻滞,有气郁之不运,有瘀血之失畅等等,如《诸病源候论》所谓:“大便难者,由五藏不调,阴阳偏有虚实,谓三焦不和,则冷热并结故也。”
大肠传导失常,是大便难的基本环节,故论治总不离通利大肠。一般大便难者,多有宿便内积,大便不可久留,留则生毒。故急者治标,选择生大黄、芒硝、槟榔攻下之,宿便久积,或危重者可用巴豆、甘遂、大戟等通下之。缓者治本,恢复大肠推陈致新,宜佐以熟大黄、姜黄、枳壳等引导之。但需注意,单纯通下,很难长效,长时间运用,反而会加重病情,只有针对病机,治本缓图,才有利于长远。(某地一民间中医,祖传一种通便消积丸药,有较强的通下之功,按法服之,多能排泄陈年宿便,一次即效,久用就无效了。)
大便难为标,五藏阴阳、气血寒热等为本。湿热蕴结者,清化湿热为治本;精血亏虚者,滋补精血为治本;肝郁气滞者,疏肝理气为治本;脾虚气弱者,健脾益气为治本;肺失和降者,和降肺气为治本;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升清阳为治本;阳虚寒凝,大肠不温,温阳逐寒为治本。治标较易,治本较难,大便难欲得根治,关键在治本的坚守。
治本是断根之法,但毕竟是大肠传导之病,宜用通利大肠之味佐之。我喜用大黄为佐使,若精血亏虚者,补益精血为主,大黄佐之;若是气虚推动无力者,补气为主,大黄佐之;若是阴虚液亏者,养阴滋液为主,大黄佐之;肝郁气滞不行者,疏肝解郁为主,大黄佐之;中焦虚寒者,温中健脾为主,大黄佐之。视大便之性状,而有熟大黄和生大黄的不同,便稀粘难出者佐以熟大黄,便干结难出则佐生大黄。若大便粘液、红赤脓血,多湿热伤络,大黄宜用为君药,促使湿热外泄。
古有湿热不宜下之说。不能绝对,看湿热所在何处,上焦、中焦湿热下之无益,大肠、膀胱湿热通下,则有利于开邪出路,所以治热淋之八正散用大黄。但大黄之用,注意配伍,因“证”而施,用之不当,或配伍失宜,有损伤正气之弊。《景岳全书》:“秘结证,凡属老人、虚人、阴藏人及产后、病后、多汗后,或小水过多,或亡血失血大吐大泻之后,多有病为燥结者,盖此非气血之亏,即津液之耗。凡此之类,皆须详察虚实,不可轻用芒硝、大黄、巴豆、牵牛、芫花、大戟等药,及承气神芎等剂。虽今日暂得通快,而重虚其虚,以至根本日竭,则明日之结,必得更甚,愈无可用之药。”
大便困难、排便不尽病机多种多样,有肝气郁滞者,可用四逆散加木香、槟榔、乌药;有湿热蕴滞者,可与甘露消毒丹加姜黄、枳壳;有肾燥精虚者,则宜济川煎加柏子仁、火麻仁;有瘀血阻滞者,当用血府逐瘀汤。肝阴虚而大便干,重用熟地、白芍以利肠腑;脾气虚而大便难,重用生白术以强脾运。制首乌、肉苁蓉在精血不足之便难,乌药、槟榔治气滞郁结之便难,制黄精、玉竹、玄参疗阴液亏虚之便难。若阴液亏虚,大便干结,阳明阻塞,兼肝气郁结化热,身颤栗而不安者,主以养阴液,辅以解肝郁且平肝,增液汤加制黄精为基本方,另用白芍为君,辅以柴胡、郁金、生牡蛎、生龙骨。脾虚气弱,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大便乏力而难出,见头昏神疲者,主以补脾升清以降浊,用补中益气汤加槟榔、枳实。
不少人认为大便难-尤其大便干结者是大肠积热,多用泄热通便之法。证之临床,大肠积热较少,虚实夹杂、肝气郁结、湿热内蕴者为多,每每五藏相关、升降相因、气血相互影响。大肠积热之大便难,病程较短,多有胃肠积热内实的特征,“辨症求机”难度较低,治疗相对较易。小儿便难发病日渐增多,多大便干结,数日一便,可用小柴胡汤加白芍、槟榔、枳实,关键在重用白芍和营利肠,枢机一转,津液得行,大便自然顺畅。
大便难常有开初治疗见效很快,继续服用反而无效的情况。五藏六腑的因应调节,是治愈疾病的内在根据,大便难也不例外,若是五藏气血的因应协调性没有恢复,即便大便一时得通、得畅、得尽,也很会反复,反复之后,再用以前有效的方药,就不一定能收效了。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治疗用药不当,也许是藏腑因应调节康复平台期的反应,检讨以前的辨证论治,要是证候病机判断可靠,处方用药决策正确,就效不更方,假以时日,静候正气来复,大肠传导就有康复之望,莫要因为无效而频繁更方;要是证候病机发生变化,或者以前用药不当,才调整治法方药,药随证转,逐步跟进。总之,根据证候病机,当守方则守方,当变方则变方,气滞得畅,湿热得尽,阴精得充,郁气得解,伏风得祛,大便就能顺畅。
不少大便难症状简单,“辨症求机”难度较大,很多时候需要一个药诊的过程。药诊是《伤寒论》创立的一种“辨症求机”方法,对于“辨症求机”难度大和极易反复的疾病,提高“知犯何逆”的准确性很有帮助。我在《中医之和-辨证论治的生命哲学》中已经论述,可以参考。
肠澼、滞下之大便难,多是湿热、热毒等内伏、留着大肠血分,如油入面,胶结难解,短期内难收全功,有的经结肠镜检查可见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或直肠肛门的疾病,可予当归贝母苦参丸加味,除湿热以解毒,和血以散结。久病者多兼清阳不升,故注意升清益气,如黄芪、升麻;肝郁热结者,用白芍、黄芩;脾虚湿滞,加白术、苍术。气机不畅,芳香行气之品,如白芷、木香、青皮;湿热留着血络,当活血利络,用丹皮、赤芍;湿热久羁,攻下捣其巢穴,用熟大黄、木香;湿热伤阴,用山药、生薏仁。
肠癖、滞下的大便难,艰涩不出,刚大便又欲大便,或有粘液,或有脓血,次数频多,腹部不舒。切勿将大便次数增多误作腹泻,通因通用,以熟大黄等开邪出路,令湿热、热毒外出,才能彻底痊愈。大黄通下胃肠,除肠间湿热,故便难用大黄,既可引导胃肠之气和降下行,又可泄湿热以外出,根据证候病机,或为君药主治之,或为佐药引导之。需要注意的是,大黄通下,除了湿热、积热之便难,大多为治标之法,或引导药力下行,其药量大小,要根据病势缓急而定。肠癖、滞下用大黄常配升麻,一升一降,升降相因。
肛门疾病的大便难也十分常见,与痔疮等密切相关,素有“十男九痔”的说法。分析直肠肛门疾病的病机,要结合人类的进化情况。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在脊椎动物的整个的生命历程中,姿势以爬行为主,直肠肛门和头部等在同一高度,直立之后,直肠肛门下降,位于藏腑的最下端。随着形态直立的变化,人类逐渐进化出脾主升清的因应调节机制,使清阳上升,肛门、大肠的血脉畅行,当脾主升清的因应调节能力失常,大肠、肛门等下部脏器的血脉很容易瘀滞,发生痔肿、便难。论治直肠肛门等疾病,增强的脾的升清功能十分重要。我常用补中益气汤加地榆、槐角、赤芍、丹皮、苦参、白芷等,治疗直肠炎、痔疮肿痛、肛周脓肿,效果较好。有一例肛周脓肿的女性,拒绝手术而求中医治疗,初诊时行走十分困难,不能坐位,以补中益气汤加味,守方十余剂而愈,数年没有复发。
大便难反应“出”的异常,但升降出入是相互关联的,“出”的异常可能因为“升”的失常,也可能因为“入”的失常;“出”的异常会影响“升”,也会影响“入”,故治疗大便难和肛门疾病,一则注意脾主升清之辨,辅以生发清阳之味,如升麻、柴胡;二则注意肝脾虚实之辨,和肝健脾增强运化而以“入”促“出”,或重用白芍,或重用生白术。这里的“入”,不是收敛止涩,而是内养内化。白芍味酸养肝,白术味甘养脾,至少用三、四十克以上,甚至克,促使肝和内养则能泄而便通,增强脾土实旺则能运而便行。
1.1.3临床论治宜忌大便难是一个很难根治的顽固疾病,疗效判断,不在一时的大便通畅,而在长远。即便开始就重视治疗,也不是很快就能康复的。当今病人,开始并不找中医,多是自行买点通便药,医院开一些通便药,没有“治病必求于本”,大便通畅的表面现象,或许加重病机,今后更难治疗。
不少病人只满足于当时之效,机械性地通下,病情逐渐加重。多年前有位女性病人便秘,长期服用一种叫“芦荟干块”的通便药,服药大便就解。我当时奉劝她,切勿长期地单纯通便,她一句反问让我语塞:大便解不出来你说怎么办?三年之后,这个病人结肠点状广泛出血,六年之后再来找我看病时,便意完全丧失,脾虚了,不仅大肠传导失司,而且清阳不升,气机升降已经障碍,后用补中益气汤加槟榔、白芍,数剂之后便意才稍稍恢复。有个从东北来的病人,二十多年没有便意,每隔三四天就吃一次通便的中成药,吃后就水便混杂而下,不吃毫无大便感觉,后来结肠镜检查,肠子变黑了。
求速效是当前医生、病人的通病,许多疾病因为速效,损伤了五藏的因应协调性,埋下了更大的健康隐患。肠癖、滞下的远期疗效,关键在开邪出路,湿热务清务尽。古人认为肠癖、滞下无补法,不是绝对的,如果有虚则需补,如补气可用黄芪,补血可用当归,补阴当用生地。补是鼓舞正气,更好地祛除湿热,一定要补而无滞,不能因为补而滋生湿热、阻滞气机。治疗肠癖、滞下等,补是权宜之计,除湿热、畅气机才是治本之图,升清降浊、湿热祛净,结肠炎、结肠息肉等就可能痊愈。湿热净、大便完全正常后,可用参苓白术散等健脾,善后防止复发。
1.1.4生活调护大便难有寒有热,有虚有实,寒者得温乃行,得凉乃凝,故慎寒凉的饮食,如梨、绿茶之类;热者得凉乃清,得温乃甚,故慎其性温热的饮食,如烟酒、油腻、辣椒花椒等。
肠癖、滞下是大肠湿热,辛辣刺激如烟酒辣椒当忌,热性肉食如羊肉牛肉要少吃。膏粱厚味、油腻煎炸容易滋生湿热,清淡饮食有利于清除湿热,慎滋味、节饮食很是重要。
大便难宜揉腹促运化,已在痞满一节介绍。
1.1.5用方四逆散:见咳嗽。
甘露消毒丹:方见咳嗽
济川煎:当归,牛膝,肉苁蓉,泽泻,升麻,枳壳。
血府逐瘀汤:见发烧。
补中益气汤:见发烧。
增液汤:玄参,麦冬,生地。
当归贝母苦参丸:当归,贝母,苦参。
参苓白术散:见咽痛。
1.1.6临床医案举例例一:
康男,41岁,年5月25日初诊。腹泻稀溏,大便粘液,每天4~8次大便不等,腹鸣但无胀痛,时已四月余,医院检查为乙状结肠孤立浅溃疡,多方服药未效。脉右虚弦,左虚短弦,舌淡红苔薄白。大肠湿热,流连血分,用当归贝母苦参丸加味。
处方:当归10克,浙贝10克,苦参10克,酒军6克,炮姜6克,姜黄10克,白芷10克,黄连10克,三剂,缓缓服之。因路途较远,就诊不便,带方而回,嘱如果有效可守方长服。
年6月15日复诊。三剂服完,又取四剂,症状明显缓解,今已服完四日,大便成形,一日2次,粘液消失,腹鸣未作,若饮食不当仍会有少许粘液,脉弦。继续治疗
处方:当归10克,浙贝10克,苦参10克,酒军6克,炮姜6克,姜黄10克,白芷10克,黄连10克,升麻10克,再十五剂而愈。
例二:
朱女,27岁,年4月10日初诊。左少服隐痛,大便粘液如涕,夹杂血丝,一日二至四次,大便质可,治疗一年余,没有效果。经结肠镜检查,诊断为结肠炎、直肠息肉,距肛门cm处见一出血点,9点钟位置见0.3×0.4cm大小息肉一枚。大肠湿热,当以清热除湿解毒为主。
处方:当归10克,浙贝10克,苦参10克,槐角15克,生地榆15克,升麻10克,黄柏15克,桔梗6克,八剂。
年4月28日复诊。大便血丝消失,开头有黄色粘液,便后肛门有火辣辣的感觉,后重,加熟大黄、槟榔以行气,开邪出路。
处方:当归10克,浙贝10克,苦参10克,槐角15克,生地榆15克,黄柏15克,熟大黄6克,升麻10克,槟榔15克。十剂。
年5月18日三诊。大便不成形,有白色条状物随大便而出,量不多,一日二次,便前小腹或有隐痛,肛门火辣辣感明显减轻,后重感消失,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佐以疏肝化湿,去槟榔加茵陈、姜黄。
处方:当归10克,浙贝10克,苦参10克,槐角15克,生地榆15克,茵陈15克,黄柏15克,熟大黄6克,姜黄10克,升麻10克,五剂。
年5月24日四诊。大便粘而难解,肛门火辣辣感没有出现,大便初头有极少粘液,有时大便不成形,一天一次。加白术健脾,增进除湿之功。
处方:当归10克,浙贝10克,苦参10克,槐角15克,生地榆15克,茵陈15克,黄柏15克,熟大黄6克,姜黄10克,升麻10克,生白术20克。五剂。
年6月1日五诊。大便开头仍有粘液,质稀,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弱,脾阳不足,用炮姜易白术
处方:黄柏15克,当归10克,浙贝10克,苦参10克,槐角15克,生地榆15克,白芷15克,熟大黄6克,炮姜6克,升麻10克,炙甘草10克,五剂。
年6月8日六诊。大便初头粘液少许,肛门热而隐痛,大便不成形。炮姜过于辛热,脾气亏虚,去炮姜加黄芪。
处方:当归10克,苦参10克,浙贝10克,槐角15克,地榆15克,黄柏15克,白芷15克,酒军6克,升麻6克,黄芪20克。十剂。
年6月22日七诊。白带量多,夹咖啡色。肛门热辣隐痛感消失,大便正常且顺畅,但粘液未净,湿热未除。守方不变,剂量略作调整。
处方:当归10克,苦参10克,浙贝10克,槐角15克,地榆15克,黄柏15克,白芷15克,酒军10克,升麻10克,黄芪20克。三剂
年6月27日八诊。带下净,大便粘液很少,左少腹胀痛,湿邪缠绵,去升麻,加生苡仁。
处方:当归10克,苦参10克,浙贝10克,槐角15克,地榆15克,黄柏15克,白芷15克,酒军10克,生苡仁30克,黄芪20克。五剂
年7月10日九诊。停药一周。大便开初仍有少许粘液。息肉因湿热壅滞,络脉瘀积而成,加通络散结之味。
处方:当归10克,苦参10克,浙贝10克,黄柏15克,白芷15克,酒军6克,黄芪20克,甲珠粉3克(冲服),莪术10克,五剂
年7月26日十诊。大便正常,初头仍有少许粘液。素有口疮宿疾,常一月或半月一发,自服中药后,至今三月没有复发。近来面部有少许丘疹。守方五剂。
年10年9日十一诊。大便开头仍然有少许白色粘液,停药一个多月后,白色粘液消失,经纤维结肠镜复查,除肛门乳头稍有肥大外,息肉消失,结肠粘膜象正常。近因生气,觉双乳胀痛,月经前加重,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涩。益气升清,疏肝理气,清化湿热。
处方:升麻10克,柴胡10克,地榆15克,槐角15克,当归10克,黄芪20克,青皮10克,陈皮10克,制香附10克,三剂。
年因感冒就诊时随访,结肠炎、息肉没有复发。
例三:
张男,32岁,年1月20日初诊。4个多月来,便秘干结如珠,努挣难出,左耳鸣声如蝉,饮食稍多则右胁疼痛,有胆囊炎病史,脉细弦,舌淡红苔薄白。肾精亏虚,肝郁失和,主以补养肾精,辅以和肝解郁。
处方:玄参60克,制首乌30克,肉苁蓉30克,白芍30克,姜黄15克,茵陈15克,枳实15克,柴胡15克。水煎服,五剂。
年2月14复诊。大便正常,二日一次,耳鸣轻微,右胁疼痛没有出现,要求守原方五剂。肾精亏虚和胆囊炎,短期内都很难恢复,嘱五剂服完,不要立即停药,可减少服药次数,再服十余剂以善后。
例四:
郑女,51岁,年2月25日初诊。多年来肛裂出血、痔疮肿痛,害怕手术,采取外用和内服药物治疗,疗效时好时坏。近加重二十余天,行走、坐凳都感疼痛,脉细,舌淡红苔薄白。治以补脾升清,清热解毒,用补中益气汤加味。
处方:党参24克,黄芪24克,白术10克,升麻6克,柴胡6克,陈皮6克,当归10克,生甘草6克,槐角15克,地榆15克,苦参10克,赤芍10克,丹皮10克,白芷10克,水煎服。
年4月2日复诊:上方共服10剂,肛裂出血、痔疮肿痛症状消失,停药五天后复发,已半月。治疗不变,五剂。
年5月8日三诊:停药后,感觉肛门坠重而胀,仍予原方治疗。服药至6月20日,症状消失,又服五剂停药。年9月11日因为过于劳累,口疮疼痛发作,肛门稍有下坠感,担心痔肿复发,前来就诊,要求继续服用前方,再予十剂,缓缓服之。
例五:
罗女,36岁,年8月14日初诊。精神不振,疲乏短气,纳差,大便稀粘而难解,粘液多,日数行,后重。强直性脊柱炎、肠炎多年。形体消瘦,背强紧痛,脉细弦,舌淡红苔薄白。脾虚气弱,大肠湿热,督脉亏虚,风邪内客。当先补脾清肠。
处方:党参24克,黄芪24克,升麻6克,柴胡6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连10克,蒲公英30克,白芷10克,熟大黄10克,炙甘草6克,三剂。
年8月19日复诊。乏力气短减轻,精神转佳,纳增,余无明显变化,守方五剂。
年8月27日三诊。大便顺畅如常,疲乏感消失。三天前吃桂圆肉、牛肉后,又大便不畅,次数增多,粘液多带血,矢气频,语声低微,精神差。脾虚湿热,伤于厚味饮食,仍以补脾清化为主,佐以消食。
处方:党参24克,黄芪24克,升麻6克,柴胡6克,当归15克,白芍15克,丹皮15克,槐角15克,地榆15克,白芷10克,苦参10克,熟大黄10克,山楂10克,炙甘草6克,十剂。
年9月19日四诊。大便转畅,一日二、三次,粘液很少,带血消失,精神振,续服十剂后。嘱:若十剂服后,大便正常,精神振作,可再取十剂,缓缓服之,以图根治。
注:
一、病机的认识和方药的运用为作者自己的学习和临床体会,仅供参考,照猫画虎者戒。
二、原创作品,请尊重作者劳动,未经许可,请勿收藏、转发,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pindaod.com/drhz/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