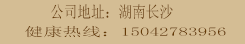点击上方蓝字“复旦外语”,和10万+一起学习
英国记者兼作家盖里·戴克斯特(GaryDexter)不是什么文坛大腕,一共才出过三本书——准确点说,应作原创一部,编撰两部——可绝对是个有趣的怪才,英国文学中模仿戏讽(parody)的技法学得尤为老到。就说原创的小说《牛津大盗》(TheOxfordDespoiler)吧,看介绍是对福尔摩斯和助手华生的刻意模仿,只不过书中的大侦探同时又是英国头号性学专家,那八个维多利亚时期的案件背后都有“孽癖”(perversion,“孽癖”者,笔者信手胡译也,我们的“80-90后”肯定称之为BT)作祟。订购的这本书尚在邮递途中,待读完再给安迪公子写上几句覆命。另一本《为什么不叫第21条军规?》(WhyNotCatch-21?),写了50部作品的书名由来,兼及诸多文坛轶事趣闻,也很想一读。这儿要介绍的是年由英国弗兰西斯·林肯有限公司出版的《笔端溅毒:从埃米斯到左拉,文坛出言伤人大观》(PoisonedPens:LiteraryInvectivefromAmistoZola)。进入正题之前,有一点说明和一个疑问。说明:编者显然在戏仿英文里的习用语fromAtoZ,故有我“大观”一译;埃米斯指的自然是被某些评家归于英国“愤青”一派的KingsleyAmis。疑问:明明是从美国上网向Amazon订购的书,投递逾两周,版权页上却赫然印着“PrintedinChina”字样,亚马逊在中国开印刷厂了?
言归正传。这是一本关于欧美文坛作家贬评、苛责甚至谩骂其他作家的书,施事者凡人,受事者,或用大白话说,挨骂者人。此乃笔者采用最原始的笨办法,从正文之后的索引中计数所得。全书按时序分五大阶段:古典时代、奥古斯都时代(18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主义时代。嫉妒、睥睨、奋矜、歹毒、以人之卑自高、同行相轻——这些可能是人性弱点冲破世俗禁锢迟早非暴露不可的恶,表现在作家的笔墨官司里,有时严肃,言类悬河,让当事人颡汗泠泠若雨;有时轻薄,黄口号嗄,显得孩子气十足。本文暂时撇开古代大家如苏格拉底、西塞罗等前几个时段,专就一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欧美晚近作家作品举例若干如下。第一,说说义正辞严类的批评。大概也是因为“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的规律起了作用,我发现多产作家往往受诘责最多。说到多产,首先会想到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e),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还有短篇小说、游记、传记、戏剧、散文等总共一百多种,虽说中国读者未必熟悉这位邮局小职员出身、做事一板一眼的人(每天定时写作,时限一到,即使稿纸上最后留下的是个逗号,也绝不续写),近年来由于英国首相带头读他,影响回归。在《笔端溅毒》中记录的批评家中有史温朋、亨利·詹姆斯、托麦斯·卡莱尔、乔治·艾略特、亨利·哈葛德等人,代表性恶评如:“特罗洛普的生殖能力特别旺盛,又行事无度。批评家们说,他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这没有什么不公平。丰产本身当然是个优点,但特罗洛普的丰产就是缠着你唠叨,叫人作呕;而他自己,我们相信,还沾沾自喜,因为比同代人给了这世界更多印刷了文字的书页。他的小说一部接着一部,非但没有明显的幕间休息,一味重叠,互踩脚跟,而且每一部大多都是超长类作品…..他是近年来写到哪儿算哪儿的伟大作家。”(亨利·詹姆斯语)特罗洛普之后,有狄更斯、萧伯纳、夏洛蒂·勃朗特等。狄更斯的作品被乔治·艾略特称之为“朽败,粗俗,窳劣……要是小说家不会写作,谁去做乞丐呢?”乔治·美瑞迪斯断言,“传世的狄更斯作品不会很多,因为与生活太不相符了。他充其量是伦敦东区文化的化身,粗线条勾勒几笔就想学做道德家……世人决不允许在我看来一肚子木头的低能匹克维克先生与堂吉诃德共享荣誉。”前面刚被人数落过的特罗洛普,也来加入合唱:“对于狄更斯的文风,不可能提出表扬,惟有批评:痉挛式的,违反语法,不按规则的滥造。对于教育自己必须看重语言的读者来说,这种文风特别讨厌。”有“悖论王子”之称的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批评萧伯纳痴迷超人,以为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布赖厄鲁斯有一百只手,世人只有两只,那么世人一定个个是残疾了;阿尔戈斯有一百只眼睛,世人只有两只,在萧看来岂非个个成了独眼龙?H.G.威尔斯说得更不客气:“萧是个战时(当然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写传单一类的脚色……医院里大呼小叫的弱智儿童,妨害别人,无法忍受。”值得注意的是,在《笔端溅毒》中,勃朗蒂姐妹中的妹妹艾米丽和她的作品《呼啸山庄》没有受到片言只语的攻讦,而对夏洛蒂那“伟大的简·爱,一个瘦小的女人”(萨克雷讽刺语),乔治·艾略特说:“我读过《简·爱》了,很想知道读者诸君欣赏这本书的理由。所有的自我牺牲都是好事,只是大家希望,牺牲是为了一个比较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一条匪夷所思的魔鬼法律,是这条法律把一个男人全身心地拴在一具腐烂中的躯体上……我更希望书中人物说话时,别像警察案情报告中的男女。”D.H.劳伦斯自有他独特的批评视角:“我敢肯定,可怜的夏洛蒂·勃朗蒂决不有意激发读者的性感情。可我发现《简·爱》已处于色情的边缘,而对我而论,薄伽丘永远是清新而健康的……瓦格纳和夏洛蒂·勃朗蒂两者都处于某种最强烈的本能崩溃的状态。性成了有点龌龊的事物,虽可沉浸其中,却又遭到鄙视。罗切斯特先生的性激情不‘值得尊敬’,一直要等到他被烧伤,瞎了眼,破了相,沦落到依赖别人的无助状态。这种失去了尊严又受人耻笑的性,到此时也才可以只在嘴上说说而已。”平素显得敦厚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女士也以为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有性压抑的毛病,她针对简恩·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而非《简·爱》,发表过类似于劳伦斯的观点:“不论‘布鲁姆斯贝里’怎么看简恩·奥斯汀,她绝非我喜爱的作家。在我看来,她全部作品的价值不及勃朗蒂姐妹们作品的一半(笔者注:间接反映伍尔芙对《呼啸山庄》有好评?)。倘有时间读她的信件,我会进一步发现她未能取得更大成就的原因。我估计,这与性有关。信件中多的是暗示,在小说里,她把自己的一半强行压抑了。”
第二,歹毒促狭的詈訾。最有代表性的是,年出版的《马克·吐温传》中引述的第13号吐温信件:“我没权利批评作品,通常我也不这么做,除非真是恨死了那书。对简恩·奥斯汀,我常想批评几句,她的作品激起我的狂怒。每次读《傲慢与偏见》,真想把那女人从坟墓里掘出来,取过她的股骨狠狠敲打她的骷髅。”D.H.劳伦斯把奥斯汀叫做“老处女”,“以负面、卑劣、势利表现英国,而不像菲尔丁那样以正面、宽容表现英国”。伍尔芙女士在私密的日记里说到自己的密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时,似已超出文字优劣判断的范畴,迹近人身攻击:“但愿对于此人的第一印象,不会使人联想到,呃,一只黄鼠狼(笔者注:原文为civetcat,即前几年引起萨斯时疫的罪魁祸首“果子狸”,为顾及国人接受习惯,译作“黄鼠狼”,其实两者也确是同属动物)上大街,臭得够呛。”在其他场合,伍女士把曼女士称作气味难闻的猫。据考证,这跟曼斯菲尔德使用廉价香水有关。英国二三流的文评家西律尔·康纳里(CyrilConnolly)——伍尔芙女士一生同他吃过一餐饭,见面“看相”即不喜此人——说起乔治·奥威尔也够刻薄的:“只要他擤鼻涕,他就想到手帕工业的现状。”因为在法庭上为《查泰莱夫人的爱人》辩护(其实是来法庭路上刚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意见)而小有名气的理查德·贺伽德(RichardHoggart)说奥威尔是“洗脑大家”,说奥氏用来用去无非是“dreadful”、“frightful”、“appalling”、“disgusting”、“hideous”这么几个“可怕”的词而已。女诗人、爵妇爱迪丝·希特维尔(EdithSitwell)说D.H.劳伦斯“活像公园里石筑毒蘑菇上的干瘪小老头”,又像“梵·高的一幅蹩脚自画像”,接着就拿查泰莱夫人的老公跟劳伦斯作比较。人家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像猛虎一样英勇作战”才落下性残疾,你劳伦斯呢?安全躲在后方家里,跟女人私通,扯着嗓门叽叽喳喳!萧伯纳是爱尔兰人,批评詹姆斯·乔伊斯,特别事涉都柏林,好像有更多的发言权,于是提出,他要封城,然后让每个从15至30岁的都柏林男子读一读乔伊斯的“脏嘴巴和脏思想”,且看其中是否有任何有趣的东西。“本人20岁时从都柏林逃到英格兰,难道今天一切都还和年时一样?”美国诗人庞德在收到乔伊斯寄来的新作《芬尼根守灵》后,写信给作者,“如此曲里拐弯的文字,其价值也许可以跟发明了一种新的花柳病治疗法相媲美?”第三,互出洋相,形同儿戏。自以为了不起的海明威教练诗人庞德拳击,恰逢英国画家兼作家温特汉姆·路易斯(WyndhamLewis)来访,海明威于是大骂庞德手脚笨拙,同时也不放过来客,说对方长了一张“蛙脸”,巴黎对这只青蛙是个过大的池塘。海明威想就此停止拳击训练,可是路易斯不让,非要看到庞德受伤不可。后来,三人饮酒。海明威仔细“看相”,发现路易斯的脸容邪恶,那双眼睛像“强奸未遂犯”。再后来,同一位文坛友人说起路易斯,对方曾见画家老是拿支铅笔在帮助目测距离和体积等等,亦即不住地measuring,这个单词后面加上个worm,即成“尺蠖”。自此,可怜的路易斯就变了一条虫。海明威恶毒,其他文坛朋友也不逊色。纳博科夫把他称作“三b”,即bells(钟),balls(睾丸,化出勇气的意思)和bulls(公牛),曾拒绝把《老人与海》译成俄语。托洛茨基的朋友、美国作家迈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嘲弄海明威的“伪阳刚”,说他的文风使人联想到“前胸装上假毛发”。海明威听了怀恨在心,时隔四年,犹耿耿于怀,这时,正好两人在一家出版社碰上了,海明威二话不说,便脱去衬衫,叫对方验看胸毛真伪,过后还坚持要伊斯特曼也敞开怀来,让人看看有无胸毛。最后两人像孩子一样扭打起来,按海明威的说法,对方“像个老娘们一样”要抓他的脸,最后被他摔倒在地!上文提到过的G.K.切斯特顿看着精瘦精瘦的萧伯纳,曾说过著名的笑话:“看你那模样,谁都会以为英国发生饥荒了。”切斯特顿本人脑满肠肥,无疑就给了萧伯纳一个极佳的反击机会:“看着你的样子,谁都会以为大饥荒是你引起的。”
***
戴克斯特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短短的前言,列举文人相轻的三个理由的同时,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理念,那就是书评文字中往往惟有贬评方是的评,而作家也惟有在跟人打起笔墨官司时往往有特别出彩的文字。他引用英国诗人和文评家埃德蒙·高斯(EdmundGosse)的话:“决不要在乎你要去褒扬什么人,但要你去贬评谁时必须非常当心。”这个理念,还有这条引语,对书评类刊物的编辑,真是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最后,说点小小的意见。可能是因为作者刚刚出道,大编辑们不太把他当回事,《笔端溅毒》这书的印刷错误不少,包括书尾索引中有两个F字部而缺了G字部。封面设计非常幼稚,初看还会以为这是本儿童读物呢。
(本文写于年3月19日,选自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余墨三集》)
来这里,和复旦的同学们一起学习
长按并识别
转载请注明:http://www.pindaod.com/drks/92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