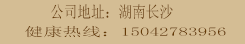点击标题下蓝色字题 上海人是瞧不起西安人的。一次,西安的一位作家去上海,上海的一位老先生,听说这位作家来自西安,眼光从老花镜的上沿处盯着他,说:西安的?听说西安冷得很,小便时,尿就像一根冰拐杖把人撑住了?作家说,西安冷是冷,但没有上海这么阴冷。老先生又问:西安城外是不是戈壁滩?作家便不高兴了,说,是的,戈壁滩一直到新疆,出门得光膀子穿羊皮袄,野着嗓子拉骆驼哩!老先生说,大上海这么大,我还没见过骆驼呢。
这个故事听了让人感到可笑,不是让人瞧不起西安人,而是让人看不起上海人了。不少上海人,呆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总感到自己如何如何的大,他不知道上海在这个大世界里,小得也只是一个点而已,小看了上海以外的世界,他也就自己看扁了自己。
稍微有点知识和文化的人,是不敢小视西安的。若论资格,西安可当爷爷,而上海就连当孙子可能也不够资格了。上海看起来比西安要富,但是,上海的一座大楼,论其价值可能抵不上兵马俑里的一个小泥人。
可能人们没有想到,就是西安这个地方贡献出一个大汉民族。中国人大部分为汉人,中国的语言称汉语,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专家被称为汉学家,日本将中医称为汉医。那么,汉又是怎么来的呢?刘邦在秦亡以后,被项羽封地在陕西汉中,为汉王。数年后刘邦击败项羽在西安建立汉朝。汉朝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开辟了丝绸之路,丝绸人都自称为汉家臣民,西方诸国因此就称他们为汉、汉人。沿袭至今。
倘若认真一点,凡汉族人要填写自己的籍贯的话,应该是西安才对,包括前文提到的上海那位老先生。因为“汉”出自西安。
但是,尽管“汉”字是千年老店,金字招牌,可“汉”并不是陕西的简称,它的简称是“秦”。翻开古籍典本,秦,原是西周边陲的一个古老部落,姓嬴氏,营养马,其先公因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而封秦地的,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开疆拓土,秦的声名传向域外,邻国于是称中国为秦。直到现在,秦的英语音译也还是中国。
说文解字一番,无非说明西安这个地方文化厚重,资格之老。世界对于中国的最早认识,不是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而是起源于陕西和陕西的西安。
2西安,古称长安,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前赵、前秦、西魏、北周等五个割据政权及汉献帝等两个末代皇帝在这里建都。尤其是西安作为中国历史前半期繁荣昌盛王朝周秦汉唐的都城,地位特别重要,所以自古就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称誉。
许多朝代建都西安,是与西安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的。西安居关中平原,南倚秦岭山脉,北临渭北山系。它位于中国地形大势第二阶梯黄土高原的东南部,雄踞黄河中游,对下游各地成居高临下之势。古人云,“自古帝者必居上游”,就是说国都要能够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另外西安所在的关中四面环山绕河,山谷河畔设关置隘,东有崤山、华山与黄河,设有函谷关、潼关与蒲津关;南有秦岭,设有山尧关、子午关、大散关与武关;北倚渭北诸山,建有萧关与金锁关;西控陇坻,上设陇关;四塞为固、金城千里,为天下形胜。足见关中形势天成,十分安全稳固。
从西安这座城市而论,它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四周山环水绕,东有灞浐,南有潏滈;西有沣涝,北有泾渭,形成了“荡荡乎八川分流”横贯环绕的局面。即人们常说的“八水绕长安”。
长安八水提供了周秦汉唐都城的生活与园林用水,同时也滋养了关中平原,使其土地肥饶。秦岭北麓物产丰富,自古有陆海之称。海者,是万物所出之区。那意思是说,西安这个地方,川原高敞,物产富集如海。
再者,西安是关中平原中部地势最为开阔的地方,若以渭河、秦岭间而论,临潼以东或周至以西,南北宽均不过二三十里,独西安小平原宽达百里,而且原野开阔,为建设规模宏大的都城奠定了基础。
关于西安的发展,秦汉都城的建设,笔者不再一一细表。本文需要着墨的是这个城市的市场经济建设。那年,我去西安,住在古都饭店,早晨饭后,想到周边的街市上购买一些东西。行走间,向道旁一位打太极拳的老者问路时,老者微笑:是去买东西是吧?你可知“东西”这两个字的出生地点就在西安,如果没有西安的“东市”和“西市”这两个市场,也就没有了“东西”这一词的诞生了。
于是,这才使我 所以,在古代的长安,要购买货物,不是到东市,就是到西市。后来“东西”一词便成为这两个市场的代名词。我每到西安,总想如果哪个高墙深院的古老住宅里,存放着当年西市作坊所铸造的钱币、陶俑和冶铸的青铜器的话,或者说那宅院就是当年中央集团的库房,那么建设西安和发展西安还怕没有钱吗?一个瓦罐拍掉,说不定就盖一个剧院,一件破铜烂铁拍掉,就可能盖一座高楼。我常常自忖,外地人是不能小瞧西安人的。也不要用这样一段民谣来编排西安人: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
三千万懒汉高唱秦腔,
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
没有辣子却嘟嘟囔囔。
没有秦川的黄土哪能造出陶俑?若是陕西人是懒汉的话,怎么打造出几千年来至今仍不能超越的文明?当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这个城市之后,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
历史的风雨送走隋朝之后,长安迎来了辉煌的唐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秦岭北麓的这块土地上,高耸起一座面积达84平方公里,人口超百万的巨大的都城。它有着最为严谨的规划,按中轴对称布局;它有着当时世界数量最多的人口,分散在如棋盘的街坊里;它有着最华丽的宫殿建筑,引东西南北竞相仿效。它的开放,它的繁华,它的光芒,令万国争相来朝。
那时的长安,是世界第一大都城,其城市方圆约35公里,是汉长安城的3倍;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1.4倍;城墙宽度为9—12米,外郭墙高一丈八尺,宫城墙高三丈五尺。长安之大,大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地步。那时,世界上还有两个赫赫的帝都,一是君士坦丁堡;二是巴格达。但是,那两座帝都和长安比较起来都相形见绌了,长安比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大7倍,较阿拉伯帝国的都城巴格达大6.2倍。
那时的中国第一街,或者说世界第一街的朱雀大街位于长安城中心线上,宽达米,这个宽度可能宽于现在北京长安街的宽度。朱雀大街从皇城的朱雀门直通南城郭门——明德门,将长安城严格划分为对称的东西两半,交错的道路呈方格网状,将城内分割为5类面积大小不等的坊,臣子百姓就在这些街坊里生活。
为了解决长安城人们的吃粮问题,唐朝的主政者,在长安城东门的望春楼下挖了一个人工湖,可通渭河,向东直达洛阳,与大运河相连。于是从江浙,从湖广而来的货物,皆用船只运到湖畔的码头,然后再运入城内。它与沿途那些为漕运顺畅而设置的转运仓一道,彻底解决了长安的经济供应问题,使唐帝国的首脑们不必因为粮荒而不时地要就食于东都洛阳,军事政治重心的一体化,终于使大唐帝国在世界上显示出它雄伟的力量。
交通是市场的生命之源,交通问题解决了,也就解决了长安的市场问题,也就开辟了它的开放道路。
因为没有交通之困,唐代的东市和西市,不仅成为这座城市经济活动中心,还是与域外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东市的面积,据文献记载:“南北居二坊之地”。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有八门。东市分布在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以西、西安铁路局以北的地方,东市由于靠近皇城,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西市,在隋代称利人市,在皇城外的西南部。作为长安城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市场,西市进行的是封闭式的集中交易,也就是将若干个同类的商品聚集起来,以“肆”或相当的“行”为单位,市内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局和平准备局。交易区也都是集中在一个四面有墙、开设市门的较为封闭的场所内。根据考古发掘成果,西市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米,东西米,面积0.96平方公里,其范围在今西安莲湖东区东桃园以东、老糜家桥以西、东桃园桥以北、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公司以南。当时的市场由令、丞负责管理市场交易,他们办公的地点,则称为“旗亭”,在亭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市场中的情况。交易的时间,还保持传统的日中而市,日落而散的办法。
市场是和政权紧紧连在一起的。五代开始,长安城结束了其作为中国都城的历史,变成了一座地方性城市,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自然环境的优越性,在北宋、金、元、明、清时期,西安仍是西北地区的一座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但后都城时代的西安已无帝都的繁华了。
由于它地处西北,告别古代开放前沿的繁华之后,接受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大大落后于沿海城市。当沿海一些城市进入摩登时代,而西安似乎还徘徊在遥远的历史之中。不!它好似被历史遗弃的小妾,美食华玉,皇堂贵府已不再属于她了。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安已经荒废沦落为一般的中等小城,在仅有唐城十分之一的那一圈明朝的城墙里,街是土道,铺为平屋,没有了城门的空门洞外就是庄稼地、胡基壕、蒿丘和涝地。也许,夜晚,在乌云遮月的时刻,那几株古树映照的古城楼上,会传出几声猫头鹰的叫啸,惊飞起一群又一群蝙蝠,但这种文学意象中存在的现实,只能更加说明了这座废都将死的无奈。
我从《大秦腔》那部电视剧里,捕捉到的最撼动心魄的讯息,就是那个时代西安城的冷落:阴森的城门楼,结冰的护城河,低矮的街坊,打铁的铺店,以及六十岁的矮小的农夫用毛驴驮着买来的小媳妇的不平世道……诚如作家贾平凹所言,那时,北京、上海已经有洋人的租界了,蹬着高跟鞋拎着小坤包的摩登女郎和穿了西服挂了怀表的先生的生活里大量充斥了洋货,言语里也时不时夹杂了“密司特”之类的英文,而西安街头的墙上,一大片卖大力丸、治花柳病、售虎头万金油的广告里偶尔有一张两张胡蝶和阮玲玉的烫发影照。那时的西安人普遍把火柴称作洋火,把肥皂叫成洋碱。街头也许有一些见过世面的人。他们谈论的话题是:蒋介石每天吃的是什么饭?宋美龄洗一次牛奶浴,需要多少黄牛去供奶?
解放前的西安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词形容它,但那时的西安写进文章中才有味道,才能让人体味到那是那个时期真正的西安,它代表古城的那个时代,包含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的韵味。因此,让人感到行将死去的西安,其实是一个永远不会死去的西安,是在人们心中沉淀并永远富有新意的西安。
3这些年来,我是常去西安的,自然也是西安巨变的目击者。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适逢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西安不仅在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在带动整个陕西、西北地区乃至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西安在历史的积淀中赋予她的不仅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老与历史文化名城,而且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与火车头,同时也是我国陇海——兰新经济带上的特大中心城市,是国际新丝绸之路上东部最大的中心城市。但是正因为西安发展了,怎么使西安这座古城的文化由隐性化走向显性化,怎么使地下的书本里的文化走上来,走出去,活起来,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了。
西安固然有大雁塔、小雁塔;固然有碑林、兵马俑,但那些地方对于熟悉西安的人,一生又能去几次呢?西安固然有高楼,有马路,有商场,但这些高楼、马路、商场和上海和北京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尤其对那些了解西安的人,每次去西安,都是想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找到一点新的感觉。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要找新的东西,在马路上,商场里是找不到的,西安新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自然的东西。一次我从钟楼向西南走进一条街巷中,古老的街道两旁出售着传统的小吃,如杏仁油茶、粉蒸肉、镜糕、枣糢糊、炒荞粉。有老樊家的腊汁肉,老韩家的挂粉汤圆,老王家的“新发生”葫芦头泡馍、王记粉汤羊血等等。一些辣面店香油坊卖的是最纯正的陕西线线辣面和关中芝麻香油。有摆摊的银匠,有吹糖人的艺人,还有白铁作坊。那位姓王的银匠,手艺是祖传的。他自十多岁跟着父亲学打银器,距今已近50年。李师傅是个厚道人,这忠厚与老实写在他憨厚的脸上。他会主动告诉客人哪是真银,哪是假银,并向你耐心地解释银子的成分。李师傅说,真银器的价值体现在材质上,其工艺也是不可低估的部分。真银越烧越白,用牙膏或洗洁净一洗,会现出美丽光泽。假银烧不得,一烧就变黑,年代稍久就会有铜绿出现。
李师傅哀叹:现在生意不好做。黄金、白金、钻石的装饰兴起之后,银器制品似乎被人看不起了。他看了一眼店外一晃而过的游人,叹了一口气:“做生意就是养家糊口。”但我以为,在现代化的西安,像李师傅这样的匠人是不可少的,少了他们,西安的文化就会变味。
从渭河北岸来到这条街上吹糖人的王师傅,那浓郁的陕西腔调的吆喝,随糖锅冒出的丝丝香甜热气,弥漫在小街的空气里。吹糖人所用的工具仅一勺一铲,一般由红、白糖加上少许饴糖组成的糖料,放在炉子上用文火煎熬,熬到可以拉丝时即能用来造型了。王师傅从糖锅里舀起一小勺糖稀,在手中揉搓成卵形,然后插入一根细细的麦管,边吹边捏,拉拉拽拽,不大会儿工夫,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精灵就出现了,神情姿态惟妙惟肖。此人吹捏糖人的动作利索,技艺娴熟,手法大概有搓、捏、吹、团、挑、揉、压、按、擦、拨等,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变化多样,让人眼花缭乱。这手艺,非一朝一夕能练就。
在一家驴肉馆的一侧,有一户庭院深深的人家,穿过一个月亮门又一个月亮门,院中的房屋,有老的建筑,也有新的楼房,但那旧室与新楼却协调得不能再协调了,怎么看搭配得都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院内有几株苍榆、数株月季,两架葡萄。几缕悦耳的琴声从楼上传来,我四周细寻,未见上楼的梯子在哪儿,但我想,弹琴的可能是这户人家的掌上明珠,刚刚考上高中的小女。
院内最后几间座北朝南的历尽沧桑的老屋里,坐着一位精瘦的老人。细问才知道,他是西安城里著名的收藏家。老人给我讲着遥远的家史,讲着收藏人的酸辣苦甜,讲着文物鉴定和收藏的知识。听着、听着,西天的残阳熏染红了整个小院。这时,我方知在老人家已呆了半天的时光。细观那古朴的屋内,坐的是明代红木椅子,端的是清代的青瓷茶碗,墙上挂的是石涛、张大千的作品。
我笑问老人:“贵府闲舍甚多,能否出租二间?”
老人笑答:“想在寒舍安度晚年?那可是需要了解西安文化的哟。”
这时我方才领悟,这小街小巷乃是西安古城的一条文化河流,贸然进入这个文化高地,看来浅薄的知识是难以与这些城里人沟通的。
那晚,我下榻于西安古城东门外一个叫香港大酒店的宾馆,与东门的城楼近在咫尺,约深夜时分,从那城墙下传来一声声秦腔,让我听得入迷,不得入睡。于是,便披衣下床,循声而去。我发现在那城墙之下,护城河之内的环城公园里,在地灯朦胧的树丛间,三三两两的人群顺城墙而去,唱的、跳的、拉的,应有尽有。有秦腔、有京戏、有豫剧,那优美的唱腔,拂掠过护城河的清波,那护城河的清波亦滋润着声声唱腔,而古老的城墙便在那唱腔的抚慰下进入了梦乡。
我想,西安,我若要是写你,这可是难得的一笔啊。
年元月4日于京西斗室
更多精彩内容请
转载请注明:http://www.pindaod.com/drks/93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