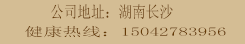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疗法 > 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里的那点事写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疗法 > 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里的那点事写

![]()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疗法 > 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里的那点事写
当前位置: 大肠息肉的症状 > 大肠息肉疗法 > 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里的那点事写
专家门诊
合理用药
热点聚焦
手术日
医学史
专家门诊给您权威参照
按今天,是国际月经日,也称为“世界经期卫生日”。对女人来说,月经并不是病,对此感到耻辱才是;中国女性不是“不怕痛”,只是没有意识到,本就不该忍痛。疫情期间,我负责科室的捐献物资接收工作,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家企业不远千里从广东给我们捐了一批卫生巾,可物资卡在武汉外围的某处货场,就是进不来。我们多方联系,搞清楚了缘由:疫情期间物流管制,非抗疫急需物资都进不了绿色通道。电话里,我们耐心解释:“卫生巾是女同志急需的东西!一线的女性医护们一天要憋在防护服里八九个小时,真的很需要这类卫生用品。”可物流那边的回答让我们有点“寒心”:“卫生巾算莫斯急需!少用一点又死不了人!等着!”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只是个小插曲,随着疫情中运力缺乏的窘境逐渐缓解,这批卫生巾最终及时送到了我们手上。女同事们非常感谢贴心的捐献人,有些同事还留下了感动的泪水——不少战斗在一线的巾帼们,是在防护服里“流汗流泪又流血”。无独有偶,我们在网络上也发现许多类似的遭遇:卫生巾被排除出抗疫必需物资的名单,医院的负责人也拒绝接收这类捐赠。同时我还发现,关于疫情中女性用品捐献的争论,在网上发酵出更深远的泡沫。一位女性博主在微博上提问:前线那么多女性医护人员,长时间闷在防护服里抢救病人,她们是怎么解决生理期问题的?卫生用品够不够?需不需要捐赠?这个问题很暖心,也很现实:彼时武汉前线防护用品缺口很大,许多医护同事们为了节省防护服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一套防护服从上班穿到下班——但在经期的同事就非常尴尬:月经是忍不住的,它时时刻刻会流下来。红色的经血可能粘在白色的防护服裤腿上,甚至漏到包裹了两层鞋套的鞋子里。穿着被经血染红的防护服工作一整天,这是多大的精神折磨啊!并且,从院感原则上说:此时防护屏障已经失效。不曾想到,这个问题却在网上遭到了讥讽和误解。有直男质问:“现在捐什么安心裤卫生巾?也不问问人家医生护士需要吗?”有人阴阳怪气:“麻烦做点实事,前线很忙的···”有些的评论“何不食肉糜”:卫生巾不够不知道去买吗?(武汉正在封城中)有喷子直接开喷了:“人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的那点事。”可能在他们看来,“裤裆”里的事,很“碍眼”吧。月经这件事,仿佛是不能放在阳光下讨论的禁忌。可悲的事,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月经这件事,还真的是“说不得”。从古至今,在国内抑或是海外,月经都与“污秽”联系在了一起。在中国古代,月经与“黑狗血”、“驴蹄子”等并列,荣膺“以毒攻毒”,“以秽制秽”的法器之列。清末的战争中,搜集到的月经布被挂在城墙上,企图对面的大炮哑火。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里这样写道:“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女性的下体,和从下体里涌出的月经,被愚昧地异化成了肮脏的符号。《圣经·旧约》中写道: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其他物件,一人摸了,也必不洁净到晚上。天主教的教义中曾这样解释:因诱惑亚当被逐出伊甸园的夏娃,被予以月经及相应的痛苦以弥补所犯下的罪过。因此直至20世纪以前,女性教徒在经期是不能踏足教堂,也不配领受圣餐的。愚昧的恐惧甚至让经血被杜撰成了耸人听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在著作《自然史》中这样写:女人的经血会使新酒变酸、使麦子枯萎,杀死蜜蜂、腐蚀铁和铜,让空气中充满恶心的味道,如果狗尝了经血就会疯掉,被这些狗咬上一口,就像被患狂犬病的狗咬了一样。在尼泊尔,直到21世纪都存在这样一专供经期的女性居住的泥棚“巢颇蒂”:她们不允许接触人群,要在这个条件极其恶劣的小棚里“赎罪”到经期结束。即使到了现代,愚昧从未远去。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印度作品《月事革命》聚焦了新德里妇女的月经之痛,在这部只有26分钟的纪录片里,对月经代代相传下来的羞辱与误解显露无遗:“流血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只有神才知道的事情,流出来的是坏血。”一个长辈妇女对女孩们这样说。“听说过月经吗?是的我听过,这是一种病,大部分女生会得的。”一群男孩被问到时这样回答着。“我们没有钱买卫生巾,只能用破布做成月经带,晚上偷偷出去埋到土里”一位中年女性这样叙述。这种“月经羞耻”(Period-Shaming)在现在社会仍随处可见,它业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在人们的脑海里生根发芽:月经是不洁的、是丑陋的、是羞耻的、是有罪的,是不能在公共场合被提及和暴露的。远到初中时期被男生抽出书包里卫生巾大声羞辱的女同学,近至在镜头前大方说自己来月经而被口诛笔伐的傅园慧;从电视广告里只能流“蓝血”的卫生巾广告,到消音谈及自己来月经的媒体采访;只要触到关于月经的“敏感话题”,社会的主流声音便仿佛本能一般掩盖与“惩罚”生理构造与男性不同的那半边天们。(傅园慧因在采访中提及来月经,已经被外媒称赞为“女权英雄”)(谈及自己处于生理期的女护士,此段话被消音)而“月经羞耻”在语境中的浓度已经高到我们觉得“理所因当”了:看看我们为了指代月经而“创造”出的那些词吧!国内有"大姨妈"、“老朋友”、“见红”、“坏(好)事儿”;国外有“鲨鱼周(SharkWeek)”、“血腥玛丽(BloodyMary)”、“那个时间(ThatTimeoftheMonth)”、“女人事(LadyBusiness)”···不恰当的对比一下,我们为男性排泄尿液,造出过多少指代词?这便是现实的吊诡:人们歌颂母亲的伟大,赞叹生育的不易,却恶毒地看待女性生育器官的正常周期变化。这是一种社会舆论的“病态”。如果说文化环境中浸润的月经羞耻是新时代女性们的心头尖刺,令她们隐隐作痛;那么月经本身带来的巨大疼痛与创伤——痛经,则是深入骨髓的痛楚。痛经对部分女性的“摧残”已经到了严重束缚女性发展、牺牲女性价值的地步。许多女性一到姨妈期就会经历惨绝人寰的煎熬,她们坐卧不宁,面如纸灰,万念俱灭,心如死水——腹部乃至腰背部巨大的痉挛性疼痛袭来,形成了严重的“应激反应”,疼痛甚至让她们弓身成虾米状,有些妹子这样描述:月经时感觉肚子里有台电锯在残忍地搅动。同时,月经时大量产生的前列腺素还会聚集在下肢、腹背部,造成腰腿处的痛,前列腺素甚至会牵涉迷走神经反射,造成恶心呕吐腹泻。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影响循环系统造成头痛、心律失常和一过性低血压。而与生理上的严重痛苦相对的,是心理上的不适与羞耻:一些姑娘由于痛经过于严重甚至会出现失禁现象,经血混合着排泄物源源不断的流下来,黏腻的触感时刻惊扰着脆弱的神经——如果这“惨案”发生在公共场合,她们必须在剧痛中时时警惕,害怕被“弄脏”的衣物落入旁人眼中,仿佛一个“抱着赃物的贼害怕被人发现”。(某博主的切身比喻)最可怕的是: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可能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与工作,许多痛经的人儿简直“生不如死”,更遑论专注于自身发展、以及发挥社会价值。根据《中国女性生理健康白皮书》[1]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有接近80%的女性伴有轻度及以上的痛经,其中超过14%的女性痛经对生活有影响。部分报告内容如下:“77%的调查对象存在痛经现象,约40%的调查对象存在中度及以上级别的痛经。18岁以下人群及轻体重人群更易发生痛经且程度更重。轻体重女性痛经的程度相对较重。数据分析表明,痛经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宫颈病变存在关联趋势,临床经验同时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史是痛经的病因。”在多起社会调查中,依据疼痛视觉评分体系来评价,一些严重的痛经甚至能达到7到8分(总分10分)——这是妥妥的病理性症状,需要医疗干预。作为与疼痛打交道的麻醉医生,我必须大声呼吁出这个浅显但被长期忽视的问题:痛经是病,疼的厉害,就要治病。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主流观点却是:”痛经嘛,忍忍吧,等你生完孩子就好了。”而吃止痛药缓解痛经这一理所应当的医疗行为,却被许多长辈极力反对——“是药三分毒”,“忍忍就好了”。由于对痛经的原理缺乏了解,对药物的副作用担忧恐惧,对疼痛危害的视而不见,乃至对自身健康权益的淡漠无知——许多中国女性在人云亦云中度过月复一月的痛经之苦。中国女性确实“太能忍了”,那么,国外女性是否“天赋异禀”、“体质迥异”不痛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海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用药物缓解痛经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常识。年,加拿大妇产科医师协会(SOGC)发布的痛经治疗指南[2]中把非甾类止痛药列为痛经治疗的首选,指南认为:除非存在禁忌症,非甾体类止痛药应当作为缓解原发性痛经,提高生活质量的首要手段。在此观念的推动下,国际上涌现了非常多著名的痛经药品牌,比如日本的EVE、美国的Midol及澳洲的Naprogesic;嚼止痛药如同服用维生素一样,是“痛经标配”。如果“是药三分毒”,那么在全球数亿口服痛经药女性的超级对照组面前,“中毒”的结局应该在网络上泛滥啊,它们哪里去了?有感于国内对痛经认知的偏差,笔者曾在社交平台上撰写了相关科普视频及文章,获得了空前蓬勃的阅读量及积极的回应:中国女性不是“不怕痛”,只是没有意识到,本就不该忍痛。令人欣慰的是:面对“月经羞耻”与痛经折磨,很多人行动起来,积极“治病”。比如,致力于女性权益保护的“全球妇女权利慈善机构英国国际计划组织”花了两年时间,推动了月经专用表情的通过。WASHUnited(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水源、公共和个人)组织在年发起了“国际经期卫生日”,将每年的5月28日定为有关月经的特别节日,呼吁人们彻底结束月经羞耻、月经禁忌等世俗观念,破除月经污名化。在英国马拉松比赛中,参赛女选手KiranGandhi决绝地不使用卫生巾,在比赛中任经血流淌,这种“行为艺术”式的抗议让她成为了对抗月经羞耻的“民间英雄”。在缓解痛经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积极寻求医疗帮助,而多地也在起草关于女性痛经的劳动福利政策,如“痛经假”等等。在我看来,破除月经羞耻的终极方法,是对女性生理结构的广泛科普,和对女性地位的实质提升。她们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在歧视与误解中被迫沉默;她们不是没有发出呼吁,只是没有渠道去倾听她们的声音。正如《印度合伙人》里的一句台词所述:“对女人来说月经并不是病,对此感到耻辱才是。”本文作者:凌肯华中医院麻醉科医师。
疫情期间自愿报名参加协和麻醉插管突击队,于武汉协和西院新冠一线连续奋战55天。
所属团队累计插管余例,参加大小抢救20余场。
曾代表团队多次登上CCTV各栏目。
个人新浪微博。
·END·
冷静
专业
关键时刻派用场转载请注明:http://www.pindaod.com/drlf/5099.html